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有种叫家仙的事物存在,说实话,我是没有见过的,但是没见过又不能保证它肯定就没有。
所以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述说的这件事情,也希望大家能用比较客观的眼光去看待,毕竟我不是想去宣传一些太富有宗教色彩的东西,表述一些老辈人所遇到的不得解释的事情这才是我的初衷。
爷爷刚刚成家的那几年,正巧是国家最贫穷的时候,穷到什么程度?说一天三顿吃不饱好像也并不能表达出那种程度,总之用爷爷的话说就是,出门你眼睛所能看到的树,都只剩下光溜溜的树干,树皮都被人剥下来,或煮或蒸着吃掉了。
平日里,大家都在生产队上工,每天都有一两顿象征性的人民gs大食堂,具体吃的东西有一小把青稞类植物煮出来的汤水,半碗糙米熬出来的一大锅粥,又或者还有一点糠包裹着青草类植物的饼。
爷爷说,这些东西不吃还好,越吃越饿,吃完了还会上吐下泻,是完完全全的吐和泻,直至吐出了黄胆水,泻到腿软,整个人也就虚脱了。
但是大家还是会吃这些食物,因为这是食物呀,人类对食物总是有着最原始的接触本能。
队里总共有三只鸡,一只公的,两只母的,这是爷爷争取来的名额,替生产队养鸡!每个月可以有一个鸡蛋的奖励,那时候这份工作可是有很多人都眼红着,鸡蛋也几乎是一户人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,而我要说的事,也就从这里开始。
饥荒的年份,每家每户都饿着肚子,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这三只鸡天天门口走来走去,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,后来爷爷为了安全,就在土房子里重新用土砖垒了一个鸡笼,大概有两三个平方这么大吧,我小时候还看到过这个鸡笼,依旧养着鸡。
有天早晨,奶奶照例去鸡笼里收鸡蛋,养过鸡的人都知道,鸡下蛋是有个大概的规律的,有的会隔一天下一个蛋,有的则是每天都下蛋,家里总共3只鸡,什么时候会下蛋,奶奶自然清清楚楚。
特别是今天,奶奶很笃定鸡肯定是下了蛋的,因为大清早的奶奶就听到了鸡笼里的母鸡咕咕叫声,那是下过蛋以后才会有的咕咕声,但是现在鸡笼里却什么也没有,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,他们还没当回事,只以为是正常的,兴许明天就又下蛋了。
等到一连三四天都出现这种情况以后,爷爷奶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在当时,如果你私自把属于公社的鸡蛋吃掉了,那可是很大的罪过,丢了养鸡的工作是小,就怕被同村的人在背后戳脊梁骨。
于是爷爷开始查找问题的原因,方法就是一听到鸡下蛋就去看着,以防小偷什么的进来。
第二天清早,母鸡照例下完了蛋,爷爷起床披上衣服提着油灯往鸡笼那边照过去,这不看不要紧,一看差点把手中的煤油灯摔到了地上。
因为在鸡窝里,正盘着一条手腕粗细的蛇,浑身漆黑,底子泛红,爷爷不认识这是什么蛇,就拿起家里放在鸡笼上的锄头,先把笼子里的鸡赶了出去,然后就去捅那条蛇。
蛇受到了惊吓,就往鸡笼外面游,爷爷抓住机会二话不说一锄头打在了蛇身上,一下子把蛇身就砸扁了一段,这下蛇也游不走了,一直在地上斯斯的翻滚挣扎着。
奶奶听到了声响,也出了房间,一出来就看到地上一条黑色的长蛇,吓得她大脑里一阵眩晕,几乎往后倒去,等到勉强扶着门框站稳了,再定眼看的时候,那条蛇的头已经被我爷爷砸扁了,一动不动的瘫在地上,只有尾巴还在一点一点的甩动。
两个人就这样在屋子里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都不知道说啥。
后来还是奶奶先开了腔,“这饥荒闹成这样,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,老鼠都活不了,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蛇呢?”爷爷沉了一下气回答道“谁知道呢,兴许是闻到鸡的味道游进房子里来的。
这下好,鸡蛋它吃了,我今天就把这个蛇拿到大队里去大家伙烧汤喝!少了鸡蛋这个事也算是有个交代。
”奶奶听爷爷说完,也没再反驳,就随他这么去了。
当天中午,大队里可热闹了,都拿着缺了口子的碗来盛蛇汤喝,队长还特许拿了两个鸡蛋打了放在锅里煮,美其名曰“龙凤汤”,滋补的很。
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,爷爷回家以后也没想什么,依旧和往常以前洗洗就睡了,当天晚上怎么睡觉都不舒服,总感觉背上刺挠,但是伸手去抓,又并没有用,所以一直翻来覆去的没睡好。
朦朦胧胧的到了第二天早上母鸡又开始了叫唤,爷爷其实一直半清醒着,就又起床,点着煤油灯去看母鸡下蛋,这一看差点没有吓死,鸡笼里一样的位置,盘着一条一样的黑色红底的蛇!
爷爷心里霎时就泛起了嘀咕,显然,巧合不足以解释这个事情了,于是就又拿着锄头,先把鸡赶了出来,然后又推了推那个蛇,蛇又游了出来,爷爷心里本想着这事情奇怪的很,就把蛇放走把。
可是这个蛇却直冲冲的向爷爷游了过来,速度之快,让爷爷没有办法去做太多思考,一狠心,又是一锄头,蛇就又被打扁在了地上,奶奶出房间以后看到这个情形,顿时吓得往后倒去,爷爷赶忙去把奶奶搀扶了起来,奶奶嘴里则是在碎碎念着,“大仙大仙,这肯定是家里的大仙,家蛇出来肯定是来警告我们什么事情的,我们却连续两次打死了这个蛇,这下要遭报应了”。
爷爷本来就年轻,火气旺盛,一听这个话,也是恶向胆边生,一不做二不休,趁天还不怎么亮,就拿洋锹把蛇一铲,扔到了一个平时没什么人去的水沟里,回来以后安慰了奶奶几句,就又去队里上工。
等到第三次看到那条蛇的时候,是在第三天,一样的时间,一样的位置,这次爷爷服了软,他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些黄纸和几根香点着了,跪在鸡笼边,一边磕头一边说“对不起,对不起,不知道是冲撞了家仙”之类的云云。
等到祷告结束,爷爷重重的磕了一个头,然后再抬眼看那个鸡笼的时候,蛇已经不知所踪,爷爷当时心中诚惶诚恐,半天都魂不守舍。
第四天,家里的母鸡一连下了三个蛋,爷爷把这几个蛋藏了起来,即使后来生活再困难,也没有拿出来过。
事情过后,奶奶生了一场大病,也留下了体质娇弱的后遗症,直到今天他们二老讲起这个事情,依旧是诚惶诚恐的。
所以呀,有些东西你看不到,所以你就不信,这本是没有错的,但是大中华洋洋洒洒五千年,留下来的只会是真,即使这个时代算不得真,但是下个时代,谁又说的定呢?
下面要和大家提起的,是关于鬼打墙的事。
或许很多人会对“鬼打墙”这个事情不感冒,认为这是可以用科学依据去解释的事情,为了这个我也去查询了相关资料。
的确,资料上说“鬼打墙”是在野外行走时,分不清方向,不知道要往何处走,所以老在原地打圈,这种经历告诉他人时,他人也难以明白,所以就说是有鬼怪无形中设置了墙壁等障碍来阻止人离开,以起到戏弄或者其他的目的。
心理学上说,这是人的一种意识朦胧形态表现,人在某些时候,会产生意识模糊,失去方向感,也就是说会在一个熟悉的地方迷路,因为你的眼睛和大脑的修正功能不存在了,你以为你走的是直线,其实你走的一直是曲线,最终放大看都是一个圆。
我本人并不排斥这种解释,因为的确这是一种科学的解释。
但是也因为生在乡下,从小家里大人都在亲力亲为的做一些事,这耳濡目染在无形中向我表达出这世界可能的确有某些神秘力量时,我又对这些事情都抱有一些自己的想象,好了,话不多说,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次的述说。
爷爷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黄土地,过的是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现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可能是很美好的事情,这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可以告诉你,种田种地是最累的事情,你无法明白夏天最热的时候要在水稻田里拔草是多么的痛苦,你也无法理解秋天收获的时候,稻芒扎在身上是有多么的难受。
爷爷有三个儿子,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,但不是因为年纪小,就最受宠爱,爷爷对待大家都一视同仁。
爸爸有时候会跟我提起他小时候,他6岁就帮其他生产队放牛,春夏秋冬都没有鞋子穿,整整两年,一头小牛犊被他放养成三四百斤的大牛,而爸爸也在8岁的时候,得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30块。
这在以前三十块还是很了不得的。
但是大家也知道,爷爷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搬迁到这边的,重新做房子包括人情债都要开销,基本上是做一点钱就拿去还债了,所以这个钱基本也就是没焐热就又给了别人。
70年代挣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呀。
家境窘迫导致爸爸到9岁才去念书,那时候一学期的学费才两三块钱,但是家里还是没有,所以爸爸就一边放羊一边念书,春夏秋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,牵着4 5只羊往坡上去,等到一两个小时以后,羊差不多吃饱了,爸爸就会牵羊回家然后拿半个洋芋或者山芋放在口袋里就去学校,脚上依旧是没有鞋。
日子就这么过了几年,爸爸读书到四年级,最后到底还是没有再坚持下去,不是因为成绩不好,而是因为家中着实困难,自己也不再是小孩子,很多事情要帮助家中分担,两个伯伯是这样,爸爸也是这样。
说到这里,我觉得很是惋惜,原本教爸爸念书的一位姓吴的女老师后来也教过我,她告诉我爸爸的成绩一直很好,有时候她自己临时有事过不来,都是让我父亲上讲台授课的,他赤着脚上学的样子,这位老师一直都记得。
爸爸就这样开始了和爷爷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我想那段日子在他心中应该和天一样,是青色的吧,纯净而忙碌,悄然又无声。
在爸爸十九岁那年,爷爷做了决定,让两个伯伯出门打工学手艺,而我爸爸留在这边跟地方上一个杀猪的师傅做学徒,因为爸爸踏实肯干,平时起早杀了猪,分好就用担子挑着,去隔壁一些村子卖猪肉,在晌午的时候就能回来,下午可以到田地里帮忙做一做农活。
各位朋友在这边不要质疑我爷爷的做法,在近90年代的时候,出门打工是一件并不稳定的活计,可能很长时间都联系不上,而且似乎带有一定的风险。
爷爷爱惜自己这个小儿子,所以才决定将他留在身边,并不是不想他出门闯一番事业。
爸爸早晚勤勤恳恳的做着自己的营生,依旧担着猪肉,沿村叫卖着,他是个很聪明的人,又比较肯吃苦,所以往往其他肉匠来这个村子吆喝的时候,大家也都早已买过了爸爸担的猪肉。
那个时候,家家户户都不富裕,往往当天就算买了肉,也没有钱支付,所以后来久而久之,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习惯,那就是到年底一次性结清肉钱。
这种方式也就导致了接下来故事的发生。
爸爸告诉我说,那是1991年的时候,腊月29,他记得很清楚,过年前的一两天,他像往常一样去收账,从下午一两点一直忙到将近傍晚,钱收的七七八八,有些实在是困难的也就还是先欠着。
大家商量好以后,爸爸就踏上了回家的路,走着走着都快到家了,突然想到,有一户人家他忘记过去,因为也是将近年关了,现在不去,只能等明年,所以爸爸就回头,顶着夜间的风,又往那户人家走去,路途并不远,大概5 6里,不一会就到了。
敲开了门,那户人家显然对现在这个时间还来要账的爸爸并不友好,说了大半天,大概意思也还是先给一点,其他的来年再结清。
毕竟已经很晚了,冬天的夜里很冷,爸爸也懒得多说就向他们要了一口热水,答应了,又走上了回家的路。
原本我家就是住在村子的最南边,乡下人家都知道,房子的大门基本都是朝南的比较多,所以我们在村子里也是最前面的一户人家。
路在村子后面,靠北,爸爸回家一般都是走大路,如果时间还早的话。
当天从那户人家出来,已经将近是八点半左右,冬天的夜里除了冷风呜呜的吹着和一两声狗叫,其他基本没有一点声音,天上像刷了一层墨,抬头什么也都看不见,没星星没月亮,孤寂的紧。
不过还好,爸爸还有一把手电筒,这夜里有个光和没有光对人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心境,所以他也没有想什么,就一直往家走。
原本应该是走大路的,但是大路一直绕到村后,他可能当时也是心里犯懒了,就想着走小路,抄近路吧。
我家门口往南两百米的样子,是一片小山包,山包上前面是开垦出来的菜田,和我家遥遥相对。
菜田往后就是一片东西向生长的树林了,树林也不大,估计有个几十亩的样子吧,再往南,就是一些坟包。
对于乡下人来说,落叶归根是天一样大的事情,逝去的亲人也应当就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,所以南边的坟包很多都是附近人家的亲人所安睡的地方,爸爸平时对自己家门口的这些环境早已熟悉的不能再熟悉,况且这边的坟山里还都是基本同村的一些先辈,所以这也没什么好怕的了,他踏上了这条羊肠小路。
小路两边还是有很多泛黄的杂草的,想来是因为这条路走的人比较少吧,风一阵一阵的刮过来,吹到树上带动树叶一阵哗哗的响,吹到草上带动枯草一片一片的扬起又倒下。
夜里一旦走到了条小路,我想再胆大的人,心里也总会是有点犯悚的吧,爸爸在那时候也不外如是。
他加快了脚步,想赶紧走过这条小路和树林,但是越是害怕就越是容易受到惊吓,突然,在前面一个坟包的墓碑后面就能看到两个碧绿的眼睛在往这边看来,爸爸的手电筒只是对着那边一扫而过,但是那种碧绿的幽幽的眼神,他至今难忘。
那东西和手电筒这边对视了一眼,就往坟包深处隐去了,很快就不见了踪影。
爸爸因为这次猝不及防的对视,愣在原地好一会,心脏剧烈的跳动着,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重新退回大路。
等到稳下心神,年轻人的热血占满了他的胸腔,这朗朗乾坤,我一没做坏事,二没对不起他人,我怕个鸟,于是就又大踏步的往前走。
等走到那块墓碑附近时,爸爸脑子里说不怕,但是身体却还是有意无意的往碑那边转了一下,想着是不是能看到刚才的东西,果不其然,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,在枯草从边看到了一个直径十多厘米的小土洞,一只黄鼠狼的小脑袋正飞快的想缩回洞里。
查明了绿眼睛的主人是黄鼠狼以后,爸爸胆子又大了起来,拍拍胸脯往家赶。
这一路倒是没有再遇见什么,除了一阵一阵的风还在吹着,其他倒是天下太平。
紧走慢走半个小时过去了,爸爸仍旧踌躇在这条羊肠小道,手电筒的光原本就很昏黄,光圈又大,光照下来中间有一大块都是黑色的斑,往前照过去,一眼看不到头,都是这条昏黄破败的小路。
等到又折腾了一个小时以后,手电筒彻底告了吹,十分钟以前照出来的光大概勉强能看清自己的脚背,现在则是完完全全的不再亮了。
爸爸就这样完全陷入了黑暗中。
东边冷不丁的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,扑楞楞,差点让他跪倒在地,他现在后悔了,就应该走大路的。
估摸着现在时间也快十点半了,爷爷奶奶还在家等他回去,心里满是懊悔。
人在这时候,完完全全就是在靠着本能往前慢慢的探摸着走,深一脚浅一脚的,衣服裤子也沾满了土灰。
冬天的夜里,风刺骨的刮,一个人在这坟地小道中,趟着黑往家的方向走。
也不知过了多久,身体感觉有些疲累了,很想找个地方能避避这风,但是又不敢停留,仍旧只是慢慢在往前摸索,手电筒他紧紧的握在手里,我想在当时,这算是当时父亲身边唯一的精神支柱了吧。
在又是一脚踩进沟里以后,爸爸突然想到了这个地方离我家本就不远,爷爷奶奶平时一直也都是等他到家以后才会关门睡觉,会不会自己在这边呼喊,而他们刚好听到以后就来接他呢?
夜深人静,万般俱寂的时候,爸爸鼓足了勇气,大声喊出了那句“爹爹”,不喊还好,一喊出声,几阵突兀的扑楞楞的声音传入耳中,爸爸心头又是猛的一缩,随后便是一阵麻木。
这句喊声似乎除了惊动了一些夜里的鸟,然后就又被风不知道刮去了哪里。
有些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轻言放弃,但是还有种人在越是困窘的时候,越容易去反抗和挣扎,我爸爸就是后者。
他眉头皱紧,手中紧紧的握着电筒,又开始了大声呼喊,一声高过一声,一句传远一句,终于,在他喉咙已经嘶哑了不知道多久的时候,他抬头突然看到家的方向有一束光往天上照了照,爸爸瞬间心中一阵悲伤,果然老父亲还在等他回家,刚刚肯定是去借电筒了,现在就要来接自己了。
他心间瞬间放松了很多,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,坐了下去,双手缩进了怀里,静静的等着爷爷过来。
事后等到爷爷找到他的时候,说那时候爸爸已经睡着了,怀里紧紧的抱着一个手电筒,坐在一块墓碑的前面,那里埋葬的是同村的一位老人,看着我爸爸光着屁股长大的老人。
这里事后等到爸爸到家,看了看时间才9点,心里也是一阵惶然。
第二天,爷爷带着我爸又回了那条路,买了一些香烛贡品和这些住在这里的人说了一些话就走了,从那之后,爸爸夜里没有再走过那条路。
鲁迅说,世上本无路,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。
我后来想,如果有条路走的人不多,那么那还能叫路么?
1978年的时候,爷爷40岁,当值虎背熊腰,年轻力壮。
他向来是负责队里的粮食供给派发以及人员工作的安排,因为他做事情光明磊落,为人亲和,所以也就比较服众,大家都很敬重他。
我们这边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座庙宇,具体供奉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清楚,听说是什么观音。
爷爷说这座庙是他带着好些人,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盖成的,时间就在1978年。
大家都知道,乡下的庙宇盖好之后,配套肯定还要搭建一个戏楼,因为庙里逢年过节都会举办庙会,届时会请一些草台戏班子来唱戏,那时候大家就会放下手中的事情,换上干净舒适的衣装,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趣,凑成一片繁华祥和的景象。
但是这世界有明就有暗,有白就有黑,树木花草发散于大千世界,就必须要有根须牢牢的扎在土壤,庙宇戏楼光华的背后,也肯定隐藏着别人都不知晓的过往呀。
爷爷在接到让他带人建造戏楼的通知时,整个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,因为自己一不懂技术,二没有人工,队长又怎么会想到让他来带着人去做这个工程呢?原因就是因为服众。
当时正处国家贫穷的时候,生产队里有时候年底都发不满个人口粮,但是上面下来视察的领导又说要丰富地方民众的文化生活,提高大家的精神消费水平,所以镇里在播下来一小笔物质补助后,就要求大队里尽快建造好这个庙宇和戏楼。
这个决定意味着,很多做这个活的人在那年都不一定会得到对应的工分或者物质报酬,话说白了,没有人是傻子,所以自然也就没什么人愿意做这件事。
出于这种情况考虑队长就只能找到爷爷,因为爷爷平时都和这些人在一起,知道他人缘好,只有他比较好调动这些人,也知道怎么才能去使用这些人。
事情落到头上,不管怎么样,爷爷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始四处联系人,千方百计的说好话,拍胸脯打包票说工分跑不了,这才凑到了一些人开始着手干活。
建造庙宇的一开始,需要先平地打地基,这个活急不来,因为如果你的基础没有打好,那么往上加盖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梁柱子发生偏差,导致房屋的重心不稳,这样下来房屋的寿命也就短。
好在大家都是庄稼人,不管干什么活都是自己亲自上阵,所以对于造房子也本就有心得,一段时间下来,这庙的基础也就打的差不多了。
众所周知供奉着菩萨的庙宇都是只有一层的,而且庙顶也几乎都是三角形的拱顶,那时候因为条件有限,所以主梁和侧梁上用来承重的只能选择比较粗的毛竹,这种竹子基本都生长在向阳面的山上,因此爷爷就只能带着几个人,拿着工具去山上找合适的毛竹。
一行人中,有一个话比较多的,叫发伢。
平时干活总是有小动作,要么是肚子疼,去哪边一蹲一个小时,要么就是做半个小时,休息一个小时,爷爷虽然话不多,但是这些也都记在了心里。
一路上就听到发伢在抱怨着“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砍竹子哦?”“砍个竹子怎么要这么远?我家屋子后面就有竹子,怎么不用我家后面的呀?”
“天天做这个吊活,也不知道有钱没钱,力气花了不少,现在还走这冤枉路,就怕晚点领导说话不算话哦。
”这时候同行的另一个木匠打断了他的话,调侃道“发伢,你刚刚说的有道理啊,去你家房子后面弄竹子吧,也省的我们往山里走了,你家那竹子小虽然小了点,但是多砍一些应该也能用啊。
”发伢听到这话,更来劲了,像是打了胜仗一般,手舞足蹈的说“那可不是,以前我还总嫌屋子后面有竹子,到夏天就招蚊子,没想到这竹子还能盖菩萨堂啊,吴组长你觉得怎么样?用我家后面的竹子吧,省的大家一起走了,我给你算便宜点,一根一毛钱怎么样?”
我爷爷听到后就回答说“你家后面那竹子那么小,砍下来菩萨堂两头都搭不到边,要了有什么用?再说了,这是为菩萨做事情,就算砍了你一点竹子,你也应该觉得光荣,还说什么算钱?”
发伢一听不高兴了,瞪着眼睛说“怎么不算钱,拿别人的用,就像是借债,那就得算钱,你可以不用我的,但是用了就得给我钱!再说了,现在这年头,人都吃不饱,还兴出来说盖什么菩萨堂,我一开始都不想说,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菩萨妖精鬼怪,要真有,那我就可以天天都大鱼大肉,我也经常都做善事,怎么就得不到一个好报?那些个吃的肚大腰圆的领导下来,动动嘴巴说一句盖一个菩萨堂,我们这些个人就要做死,天天么起早贪黑的,都不知道过年有没有钱和粮食,我们图什么?娘的,弄得老子一肚子的鸟气,不干了,走了!”
他说走就走,回头大踏步的往家走去,原本手里拿的绳子也直接就扔在了地上,这可把我爷爷气的脸一阵青一阵白,没办法,发伢说的有道理,事实就是这样,自己虽然保证说做这个活过年有钱,但是这也得上面给钱才行,爷爷自知理亏,也就只能随他去。
其实一开始做这个菩萨堂,爷爷是抱有一点点私心的,因为他年轻时候遇到过几件足以让他诚惶诚恐的事情,所以他也就相信这些神啊佛啊什么的,现在想着自己在带头盖这个庙堂,以后或许能得到菩萨的保佑,以后的日子也就好过一些。
哎,摇摇头,他甩掉了这些想法,捡起地上的绳子,继续和其他人往山里走,一路上大家都在安慰他,也不知爷爷听进没听进去。
几天以后,庙堂要上梁了,大家伙当天格外的卖力。
等到齐心协力的把房梁弄好,已经将近中午,按照惯例,房子上梁,房主应该要请干活的师傅们吃顿好的,所以大队里当天也弄了一些酒水过来,大家洗洗手也就坐上了桌。
这时候,爷爷突然想到发伢今天没有来,于是他就想发伢是否还在生气,虽然发伢有事没事总是躲懒,但是怎么说,他也是参与了庙堂的建造,而且前面也的确是自己叫他来帮忙干活的,于情于理都应该去喊他一声。
打定主意,爷爷就招呼各位先吃,自己去喊一下发伢。
发伢的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北面,周围就只有他一户,其他最近的离他家也有好几十米。
爷爷走上前发现发伢的门没有锁,想来应该是在家,于是就推开门,走了进去,印入眼帘的先是一幅破旧的画卷挂在堂前,画面上是一只老虎站在山头上,旁边有一道瀑布,雪白的水花往下倾洒,中间题字“猛虎撼山”,只不过这画的年代应该久远了,卷轴的两边遍是细丝蜘蛛网和灰尘,画老虎的部分也早已经蒙上了一层细细的薄灰,这么细一看反而使画面有些蔫嗒嗒的。
堂前的西边是发伢所住的房间,还没走到门前,一股劣质的烟味混合着汗臭衣服的味道就传入了爷爷的鼻子,爷爷浑然不在意,就喊了一声发伢,然后推开了他的房门。
只见发伢正坐在床头,头发就如同冬天破败的杂草,东一倒西一歪,两眼遍布血丝,脸上的表情木讷,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,手指间夹着一只点着的白色金丝猴烟,床边的地上扔满了嘬过的烟头,一些没洗过的衣服杂乱的堆在一边的墙角。
爷爷看他的精神好像不太好,就又走到他面前,拍拍发伢的肩膀说,“发伢,怎么昨晚没睡啊?精神这么差,庙堂的房梁上好了,我来喊你去吃饭的。
”发伢听到了话,瞳孔猛的一缩,然后抬头定睛看了一下我爷爷,眉头一皱,又自顾低下了头,一只手插入头发中,狠狠的抓了两下头皮,随后猛的吸了两口香烟,喉咙里发出了嘶嘶声,几秒后又噗的一声,全部吐了出来,于是屋子里就升腾起了一阵白色的烟雾。
“吴队长啊,我这两天晚上遇到事情了,是以前从没遇到过的那种事情,这事把我弄得人也呆头呆脑的了。
”爷爷听完这话,愣了一会,就对发伢说“你这屋子太闷人了,我去端两张凳子,你披件衣裳,我们到门口去说。
”于是就自顾自的去堂前端了两张小凳子,随后走出了大门,将凳子放在了外边,自己坐了上去。
过了几分钟,发伢身上披着一件衣服,出了门就坐到了爷爷的旁边,伸手递了一支烟给爷爷,两个人吞云吐雾了一会,发伢开了口“那天下午我回来以后,因为人有些疲累,就想洗个澡躺床上去睡觉,四处想找我的搓澡布,找来找去找不到,我就随便打了盆水就把身上擦一擦就躺在了床上。
等到一觉睡醒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了,我也不知道是几点,反正我开门看了看,村子里到处都是黑的,一盏灯都没有,只有月亮挂在天边,想来应该是很晚了吧,那时候我肚子饿,就寻思着去煮两个山芋好了。
我关上门点着煤油灯放在堂前,说来奇怪,明明我关了门了,那煤油灯的火苗却是一直在闪抖着,好像一不小心就要灭,那时我也没在意,就提着放在灶头上,然后自己去灶膛里点火,等到把火点着的以后,我就提着灯去东边的房间拿山芋,你也知道,原来那个房间是我老娘住的,现在她人不在了,那房间平时我也就堆放一点东西,旧衣服啊,山芋什么的。
走到房间里,我找来找去又找不到,放山芋的框子空了,这可把我气的不行,我当时也没细想,只觉得家里可能是遭了贼,都是干这点活害的我人不在家,现在好了,山芋也没得吃了,我一脚踢翻了那个框子,就往我自己的房间里找,想看看我的床脚的米还在不在。
万幸的是,床脚米缸里的米还在,当时我也是饿得不行,骂了两句以后就抓了一碗米,打了点水胡乱洗洗,倒进了锅里。
厨房里米饭是越煮越香,我为了省点煤油就灭了灯,照着灶膛里的火光做事情。
说来也奇怪,明明人在烤火,结果这后背却总是凉嗖嗖的,我就又转过身来,想把背也烤一烤,这一回头冷不丁的就看到一对亮黄的大眼珠子在直勾勾盯着我看,那眼珠子中间一条漆黑的线,好像能把人都吸进去囚禁起来,我吓得从板凳上掉了下来,那东西一下就从柴堆上跳了下来,还在盯着我看,他娘的原来是一只黑猫,老子当时就一脚甩过去,把那只猫踢的老远,它喵呜一声惨叫,然后就窸窸窣窣的不知道跑去了哪里。
那之后,背上那种凉飕飕的感觉就没了,我就又坐在了灶膛前面,火烘在人身上,我不一会儿就感觉脑子里昏昏沉沉的,直想睡觉,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突然就从瞌睡里惊醒,像是有人猛地推了我一把,我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。
用手搓了两下脸以后,于是我就抬起头想看看饭煮的怎么样了,这一抬头,我又借着火光又隐隐约约的看到灶膛尽头的黑暗里,似有似无的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慢慢的往我房间移动着,像是个人,浑身黑色的人,这时候,除了灶膛里木柴爆裂之后偶尔的噼啪声音就完全是一片寂静,我当时第一反应是,那个贼偷又想来偷我的米,于是我恶向胆边生,你不仁我不义,等他消失在黑暗里之后,我拿起厨房里的菜刀,然后也轻手轻脚的站起来,跟了上去。
我离他大概有十来米,在他前脚正好跨进我房间以后,我猛地发力,往他的方向就跑过去,嘴里喊你这个狗东西,偷我的东西,我今天就砍死你。
就在我要跑进房间的时候,那房门猛地在前面关上了,发出了嗙的一声大响,我用力又是一脚,就踹开了房门,奇怪的是我脚踢到门上,发现门上没有什么力,刚刚只是关了,但是没合上锁扣,虚掩着,所以我一下收力不及时,连人带刀就摔进了房间里。
这一下我更加生气了,赶忙爬起来,用力把门一关,呵,今天晚上是真的要见血了,门我关上,谁都出不去。
我就让你这个贼偷死在这里!等到我适应了黑暗之后,就借着窗户外面照进来的月光开始打量自己的房间。
首先我看了床尾,那正好在我的右手边,我手里拿着刀,愤怒充斥着我的脑子,这时候我一点也不怕,结果床尾除了一个孤零零的米缸就什么也没有了,然后我又把目光移到左边的墙角,那边是我放换洗衣服的,也是黑幽幽的,并没有一个人,而床上空荡荡的除了一床薄被子就什么都没了。
那么现在整个就只剩下房间最西南角落里,那个破旧的黄色衣柜了。
我轻轻的走了过去,右手全是汗,但是我依然握紧了这把菜刀,我感觉这把刀现在是我力量的来源。
月亮光照到房间的地上,而我现在走到了放东南角旧衣服的角落,柜门上有一面缺了角玻璃镜子,我就这样隔着月光,和镜子里拿菜刀的自己遥遥相望。
镜子里我的,满面幽暗,手里的刀隐隐的反射着寒人的光,我似乎感觉这镜子里的我在嘲笑着现在的我,这柜门明显开了一条缝,你都不去打开,里面是偷了你一整框山芋,现在还想再偷你米的人,你都不敢去打开。
老子越想越气,就跨过了月亮光,直接用手抓住柜子门,使劲一拉,柜门反手就撞在了柜子上,哗啦啦!刺耳的声音一下传入了耳朵,在这么静的夜里让人浑身发抖。
那块玻璃被撞的粉碎,全部都掉在了地上,一块两块落进了月光里,在老房子的房顶上反射出几块亮斑。
时间就好像这么停了,我没说一句话,只死死的盯着柜子里,而柜子反馈给我的,只有黑幽幽的一片。
这时候我不敢上前找,思前想后于是又是一脚,踢在了柜子上,那柜子被我踢得一阵抖,随后一声凄厉的喵呜传入了耳朵,当时我的心一揪,就像是被人狠狠的拽紧拉扯着,人差点直接倒在地上,你都不知道,为什么这声音就这么刺耳。
一声嘶叫过后,随之而来的是那只大黑猫,一下子往我脸门上窜过来,依旧是那个黄色的眼珠子和幽深的黑眼孔,我束手无策,就举起手来用刀一撇,那只猫被我直接砍翻在地上,血溅在我的脸上,还有些温度,气味则是直接从我的鼻腔冲入我的脑门,我感觉自己一阵眩晕,就往后坐倒在了地上。
那时候我大口大口的喘着气,仿佛做了自己这辈子最累的活,而那猫已经没了动静,在地上一动不动,血还在慢慢流出来。
是往我在的方向流过来,我扔掉了刀,移到了另一边,就这么坐在地上看着,自己也慢慢变的麻木。
”
发伢这时候停了下来,抖动了一下手指间香烟落下的烟灰,眼神空洞的看着前方,随后重重的叹了一口气,把香烟放进嘴里,又是一大口,伴随着喉咙里发出的嘶嘶声,随之而来的,是一阵白色的烟雾,让人看不清他的脸。
“在地上坐了不知道多久,我站起身来,好像用完了我全身的力气,我又走进了堂前,去拿了一把扫帚,转身就走进了房间,想清理一下地上的狼狈。
结果,刚刚真真切切被我砍死掉在地上的黑猫,此时早已经不见了踪影,只有地上的一滩血迹,告诉我,刚刚那一切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情,我扔掉了扫把,两只手抱着头,嘴唇不停的抽搐,然后两条腿发抖着慢慢的往后退,我一下瘫坐在了床板上,我不相信眼前的一切,甚至我不相信自己,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?我是遇到了什么?
寂静的夜里,我很清楚的听到了嗒嗒嗒的声音,那是我恐惧过后,上下牙齿互相发抖碰撞发出来的声音,我想那时候我的目光涣散,定定的看着那摊血,肯定像是一个疯子,不知道我坐了多久,然后就在我转身想去睡觉的时候,突然感觉到一种冰凉刺入了我的骨髓,我低头一看,一双黑漆漆的手就这么抓着我的脚脖子,那手连带着手腕也都是黑漆漆的一片,还没来得及把脚扯回来,我就先被那双手用力的往床底拉去,我两只手抓住床板,想与之角力,但是不消几秒钟,我就整个被带进了床底,我想我应该是直接晕死了过去。
等到醒来时候已经是第二天,我颤颤巍巍的看着床底板,感觉自己像是被塞进了一口棺材,手脚发麻而冰凉,浑身酸痛而僵硬,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久时间才爬出了床底,也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才开始清理地上的血迹。
这之后的几天里,那东西每天晚点都会来拽我的脚脖子,我能看的到那双黑手,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个什么,我亮过灯找过,但是床底下什么都没有,但是每次我睡着,它又总是会在床底下伸出手来拽我。
总之我想,我算是快要死了吧。
是呀,我应该是快要死了。
”爷爷听到这里,兀自深呼吸了一口气,站了起来用力拍拍发伢的肩膀,打断了他的自言自语,“前两天还在说不信,今天就这样了,别多说了,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唬自己,走吧,我们去吃口庙里的上梁饭,说不定你也好去去晦气!”发伢抬头看向了爷爷,又低下头来,随后像是做出了重大决定“也是,他娘的,说不定就是我多想了产生了幻觉也不一定,走,去吃饭!”当天吃过午饭,发伢就留在那边干起了活,认认真真的一直到庙宇和戏楼都建造完全,而这件事他对任何人也都没有再说起。
再后来,他争着做了这间庙的庙祝,平时都会去庙里看看打扫打扫,凡初一十五也都会很早的就去开门迎接香客。
直到有一天,他被人发现在戏楼的台底下自缢了,从此以后那个庙也就破落了下去。
后来2000年初,这个庙重新翻盖,动工的时候我还小,只记得有那么一天我陪着爷爷站在那块地方看了很久很久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渡善阁出马出道劝善网 » “保家仙”真的存在吗?

 渡善阁出马出道劝善网
渡善阁出马出道劝善网
 东北出马仙“职业捉鬼人”带你走近灵异事
东北出马仙“职业捉鬼人”带你走近灵异事 黄天龙是哪位仙家?黄家仙黄天龙的来历
黄天龙是哪位仙家?黄家仙黄天龙的来历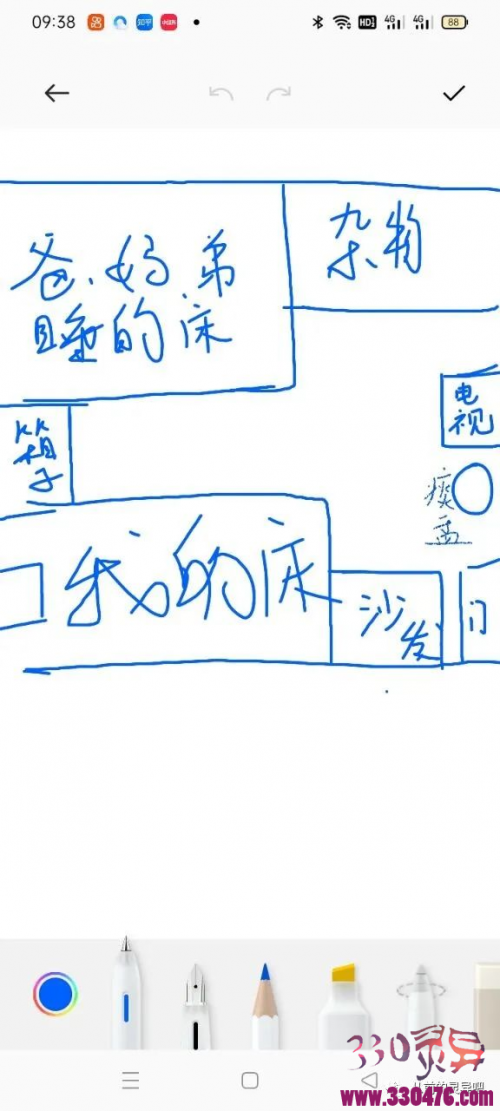 “请仙上身”时要打嗝打哈欠?
“请仙上身”时要打嗝打哈欠? 东北七十二路仙家介绍
东北七十二路仙家介绍 出马仙(带仙缘)梦境解析经验讲解
出马仙(带仙缘)梦境解析经验讲解


